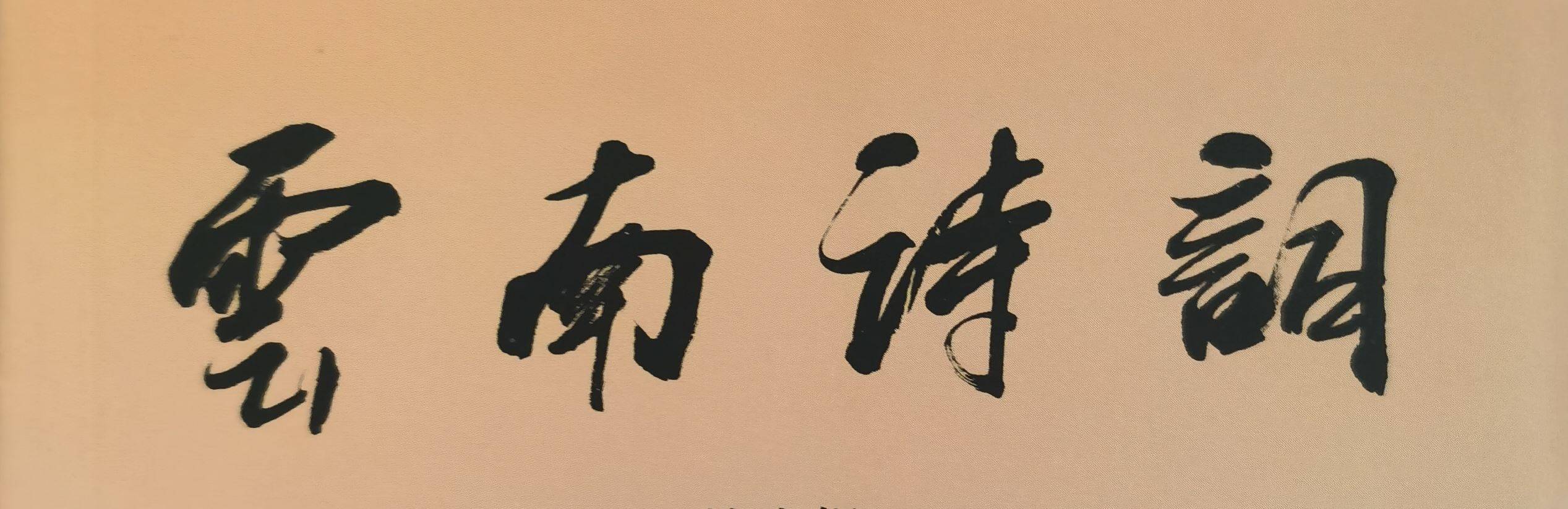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诗长、诗友:
大家下午好!值此丹桂飘香,金风送爽时节,全民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在全国各地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今天出席本会与省老干部诗词协会和省老干部活动中心联合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的吟诵、朗诵展演,我感到十分荣幸,深感振奋!
回眸历史,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进行了14年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反侵略卫国战争。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超过3500万,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6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沦陷。然而,面对艰危凶险的处境,面对“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生死较量,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儿女在抗战中有着不凡的贡献,并彰显出伟岸雄强的“云南精神”,这种精神是聂耳激昂崇高的爱国精神,这种精神是六十军勇猛强悍、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是二十万各族民众风餐露宿、不畏艰险修筑滇缅公路团结奋战、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张问德《答田岛书》大义凛然、气节忠贞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西南联大守护文脉、刚毅坚卓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曾将抗战精神凝练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云南的抗战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光辉体现。今天,我们纪念抗战精神不仅为了铭记历史,缅怀英烈,珍视和平,也为了激励国人踔厉奋发、团结一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9月3日,盛况空前的阅兵仪式不仅展现了祖国威武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气势磅礴的民族凝聚力,也昭示了我国坚定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信心和勇气,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诗长、诗友:
中国传统诗词自诞生之时起,便饱含家国情怀。一部中国诗歌史,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眷怀故国母邦的历史(虽然国家观念并非都指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诗经·秦风》讲“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屈原讲“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曹植讲“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阮籍讲“临难不顾身,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戴叔伦言“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骆宾王言“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李白言“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杜甫讲“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李贺讲“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清照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苏轼说“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张元幹写道“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岳飞说“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陆游说“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近现代以来,谭嗣同讲“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秋瑾言“金瓯已缺终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杨沧白讲“万方忧愤切,谁忍独逍遥”,邵力子说“是丈夫,皆应继风徽,收京阙”,钱来苏言“莫负昂藏七尺躯,忍看华胄籍为奴”,谢晋元言“勇敢杀敌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有着深厚的、浓烈的爱国情怀。
抗战诗词较广泛深入地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抗战14年,中华民族历经苦难、浴血奋战,其间产生了大量抗战主题诗词。这些诗词慷慨悲壮,既秉承传统边塞诗爱国尚武、英雄豪壮的精神和诗史传统,又在抗战环境中表现出新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气象,发出时代强音。”陈懋恒《抗战百一诗》记述北平战斗、台儿庄战役中以身殉国的英雄群体,陈友琴《惊闻八百壮士遇难》记录震惊中外的“八百壮士”四行仓库保卫战。还有不少诗作,以传记方式为英雄塑像,颂赞左权、蔡廷锴、张自忠、赵登禹等抗战英雄抛洒热血甚至献出生命的故事。这些抗战诗词以诗记史,补史之阙,为我们铭记历史留下了珍贵参照,更为许许多多民族英雄树起了丰碑。”(引自周兴陆《抗战诗词三百首》)
此外,值得关注且与我们今天的活动关系紧密的是,抗战时期全国各地的诗社、文学社曾组织过各种诗歌朗诵运动,比如,延安、武汉、重庆、广州、桂林、昆明等地都出现过较大规模的诗歌朗诵运动。诗歌朗诵因其所具有的通俗性、音乐性、表演性和鼓动性,曾极大地鼓舞着民众和将士的抗日士气。云南籍诗人柯仲平在抗战朗诵诗运动中具有很大的影响,穆木天曾回忆柯仲平的朗诵时曾说:“柯仲平先生的高歌,是身体的动作,热情、声音,互相调和,互相一致的……那使我们狂奋,恨不能随着柯仲平先生的歌声,加快了我们的步伐,向着我们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向前杀去。”①1938年5月举行的边区工会代表大会上 ,柯仲平朗诵了《边区自卫军》,不仅“台下几百位朴素的工人们在狂欢地鼓着掌”,毛泽东主席也热烈鼓掌 。大会结束后 ,他写信给柯仲平,表示《边区自卫军》“很好很好”,希望他“赶快付印 ”。抗战时期,延安的“战歌社”、重庆的“诗歌朗诵队 ”、广州的“中国诗坛社”等社团在诗歌朗诵方面都有显著的贡献。
昆明的诗歌朗诵运动与《战歌》杂志有关。《战歌》1938年第3、4、5期,分别发表了三篇诗歌朗诵理论文章:徐嘉瑞的《高兰的朗诵诗》、穆木天《论诗歌朗读运动》、佩弦(朱自清)《谈诗歌朗诵》。“朱自清对诗歌朗诵的关注对西南联大的朗诵诗运动有所启示,并且与闻一多 、李广田共同创立了西南联大的朗诵诗观念:‘闻一多开其先,朱自清和李广田继其后’”“朗诵诗是政治的诗,宣传的诗,群众的诗,新体的诗,今天的诗,‘我们’的诗,综合的诗,有力的诗和行动的诗 ”②西南联大的冬青文艺社与新诗社彰显了学生诗歌朗诵运动的成绩。冯至曾回忆自己在西南联大参加“新诗社”朗诵会的情形:“在昆明时,我曾经被约请参加过几次新诗社的聚会,聚会的地点有时在西南联大简陋的课室,有时在学校附近的一所小楼上,每次开会回来,心里都感到兴奋,情感好像得到一些解放。灯光下听着社员们各自诵读他们的作品,彼此毫不客气地批评,我至今还没有忘记一些诗在诵读时所给我的印象。”
吕剑也曾谈到抗战时期昆明举办诗歌朗诵的盛况:“最近昆明举行了几次诗歌朗诵,成绩都不错,有一次,参加朗诵会的诗人、诗歌工作者、诗歌爱好者达千余人之多,这在昆明,真是了不起的举动。拿诗歌来直接的和广大的人群见面,这在昆明,恐怕还是第一次。”
由于柯仲平诗歌朗诵的广泛影响力、联大文艺社团对诗歌朗诵活动倡导和实践以及昆明学生和民众的参与性,因此,我们可以说云南诗歌朗诵有良好的传统,而今天的活动即是对这一传统的薪传。
至于吟诵,它是旧体诗词创作与鉴赏的不可忽视的途径。清代“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在《与陈硕甫书》中指出:“诗古文各要从声音正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声画妍蚩,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明人刘绩指出:唐人诗一家自有一家声调,高下徐疾皆为律吕,吟而绎之,令人有闻《韶》忘味之意。”清人沈德潜则在《说诗晬语》中讲:“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从吟诵的文类而言,有诗的吟诵、词的吟诵和文的吟诵,从吟诵的语言讲有方言吟诵和普通话吟诵,古音诵读与今音诵读;从吟诵的要求讲要注重“字正腔圆”“字正”即准确、清楚明亮;“腔圆”即吟诵时声音饱满、圆润、优美,声调婉转动听。要使腔圆要努力解决好“调其气、控其调、适其情、精于技”“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而吟诵的“因声入境”“就是随着吟诵时声音的抑扬顿挫、语速的徐疾变化和腔调的婉转曲折步入诗词的不同意境中去”,要“因声、求气、得神、入境”要有“个性表达”,要注重用韵、平仄和节奏点等。总之,吟诵是一门专门性的学问,一门具有美感的语言、语音的艺术。吟诵可以增强我们对诗文经典的感受力、理解力、想象力、审美力,可以愉情悦志,可以丰富人生的诗性和意趣。
各位领导、各位诗长、诗友:
今天我们开展吟诵、朗诵活动,其意义是丰富的,值得重视的,一者缅怀英烈、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发扬云南抗战精神;二者引起对抗战诗词的关注和研究,提高当前的诗词创作水平;三者传承和推动吟诵、朗诵艺术;第四则是加强学会之间的合作、增进诗人之间的交流。
最后,我代表学会向征文获奖的诗友表示热烈地祝贺!向为活动提供场地的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以及工作人员和服务的诗友表示衷心的感谢!预祝展演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注】①穆木天:《诗歌朗读和高兰先生的两首尝试》,载1937年10月23日《大公报》。②参见吴昊:《抗战时期诗歌朗诵运动钩沉》,载《南方文坛》2020年第1期。
撰稿:赵嘉鸿
编辑:李如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