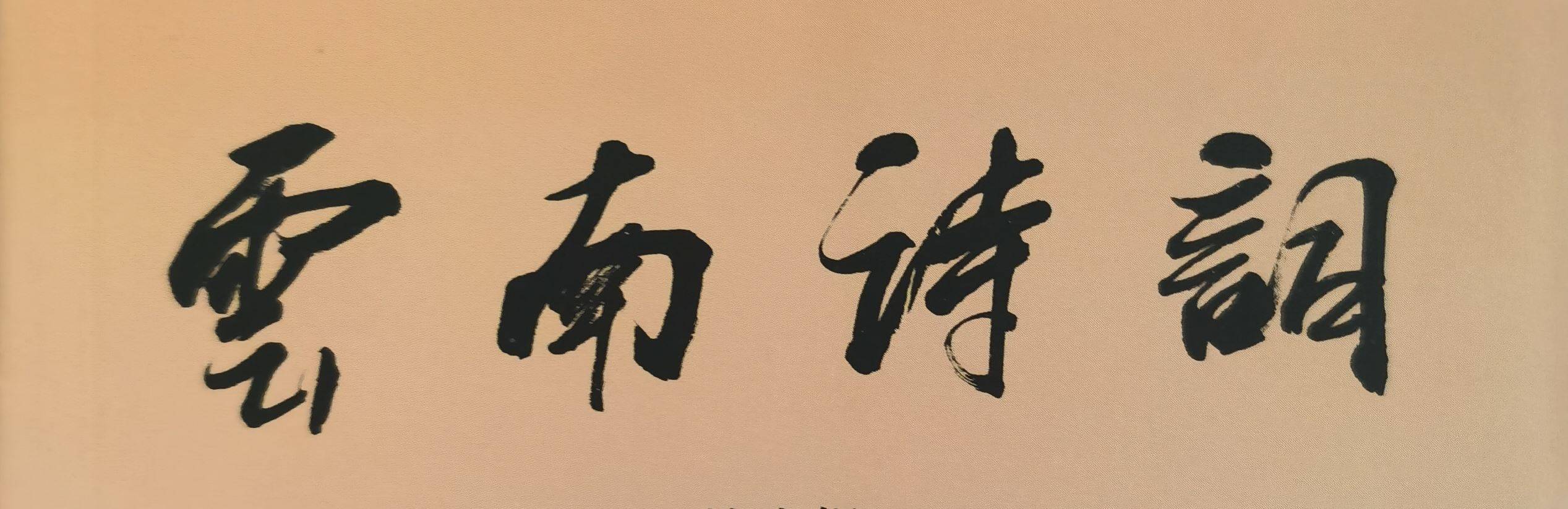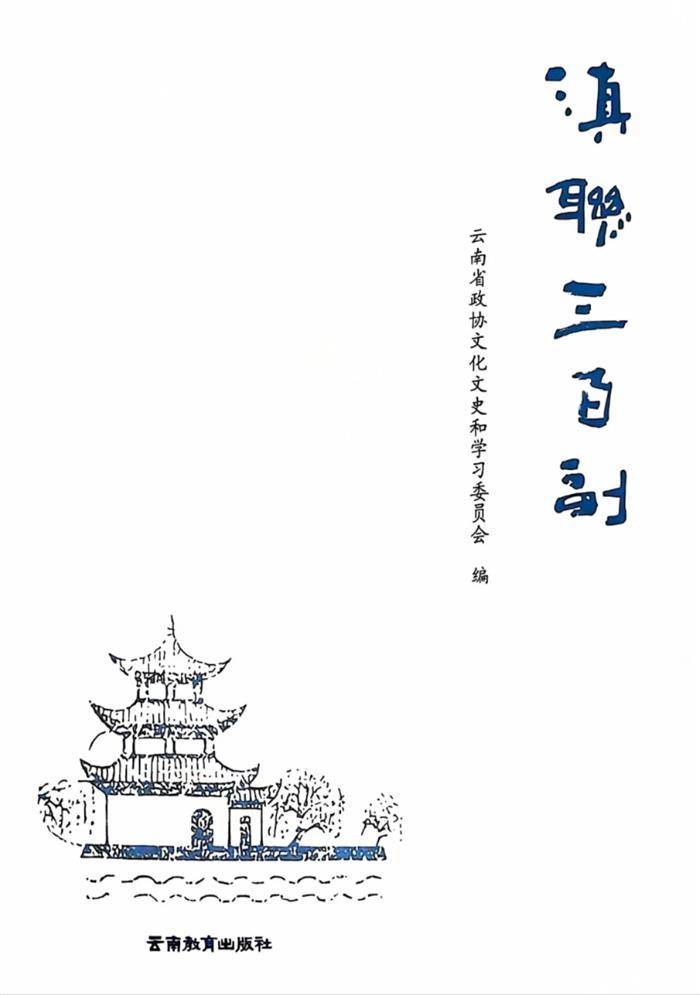
摘要:赵廷俊所撰《赠赵甲南》联,融合汉族典故与白族文化符号,是大理士族文化缩影。他嘉庆中举后多地任职推行儒家理念,归乡建宗祠刻典籍。联语借“荆树”“燕山”等传递“耕读传家”价值观,展现边疆士人对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参与。赵氏家族科甲兴盛,家规重视教育,使汉白文化相融。此联凝聚家族与地域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文化价值。
关键词:赵廷俊;联语;大理士族;文化融合;耕读传家
赵廷俊所撰《赠赵甲南》一联,“荆树栽培绿野堂,此日花萼楼前,芹沼香浮红叶句;燕山训迪传衣钵,他年凤凰毛里,鹏程远报紫泥封”,蕴含深厚意蕴。它不仅是赵氏家族“耕读传家”的生动写照,更折射出清代大理士族文化生态。联中融合汉族典故与白族文化符号,如“荆树”“燕山”等承载家族伦理与教育传承,“绿野堂”关联地域文化。赵廷俊借此联传递价值观,彰显边疆士人对中华文化共同体的主动参与,极具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
一、联语归属与赵廷俊、赵甲南关系考辨
(一)赵廷俊生平的历史拼图
据《云南通志?选举志》记载,赵廷俊于嘉庆十九年(1814)中进士,其名次为三甲第七十二名。这一记载与《大理府志》卷二十一《人物志》中“赵廷俊,字特达,喜洲人,嘉庆甲戌科进士”的记录完全吻合。清代《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显示,赵廷俊历任陕西汉阴厅同知(1823-1826)、兴安府知府(1827-1831)等职,其在任期间“兴修水利,创办义学”,政绩载于《兴安府志》卷三《职官志》。这些官方档案为赵廷俊的官僚生涯提供了确凿证据。
大理喜洲赵氏家族在明清两代共有进士17人,举人38人,形成独特的科举文化生态。《赵氏族谱?科第录》记载,赵廷俊祖父赵文魁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举人,父亲赵承业为雍正十三年(1735)拔贡,这种“祖孙三代科甲蝉联”的现象,印证了其家族“耕读传家”的传统。族谱中“绿野堂”作为家族堂号的记载,与联语中的“绿野堂”典故形成互文,暗示赵廷俊联语创作的家族文化背景。
(二)联语归属的文献学考释
“荆树栽培绿野堂”一联中的“荆树”典故出自《续齐谐记》田真兄弟分财故事,喻指兄弟和睦。《赵氏族谱?族规》明确记载“兄弟同居者奖,分爨者罚”,这种家族伦理与联语主题高度契合。“绿野堂”作为唐代裴度的宅邸,在《新唐书?裴度传》中被描述为“野服萧散”的园林,隐喻赵廷俊作为地方官员的雅量。清代云南进士周际华在《金台诗钞》中曾用“绿野堂开集俊髦”的诗句赞誉同僚,可见这一典故在清代士大夫中的使用频率。
“燕山训迪传衣钵”中的窦禹钧典故,在《宋史?窦仪传》中记载其“五子登科”的事迹。《大理府志》卷二十四《艺文志》收录的赵廷俊《劝学示子侄》文中,有“当效窦燕山之教,承裴晋公之风”的表述,直接关联联语内容。清代科举文献《科场条例》规定,生员入学需通过“岁试”,联语中的“芹沼香浮”恰指生员资格,与赵甲南的身份形成对应。
(三)赵甲南身份的谱系学考证
赵甲南之名虽未见于正史,但《赵氏族谱?世系表》记载:“廷俊公长子名甲南,道光七年(1827)岁贡生。”这与联语中“红叶题诗”的科场佳话形成时间对应。族谱中同辈兄弟命名规律显示,廷俊子侄辈多以“甲”“乙”排序,如赵甲南、赵乙北,这种命名习俗在白族科举家族中普遍存在。
赵甲南的“芹沼香浮”身份在《大理府学志》中有迹可循。该志卷四《生员录》记载:“赵甲南,喜洲人,道光七年入学,廪生。”结合联语中“传衣钵”的隐喻,可推断赵廷俊可能担任过赵甲南的乡试座师。清代《钦定科场条例》规定,考官与考生形成“师生之谊”,赵廷俊作为兴安知府,有可能在任期间主持过地方考试,从而建立这种特殊关系。
(四)文化生态中的科举隐喻
清代云南科举呈现“边疆儒学化”特征,大理作为滇西文化中心,形成独特的“士族-科举”互动模式。《云南通志?学校志》记载,清代大理府共建有书院23所,社学58处,这种教育网络为联语创作提供了文化土壤。赵廷俊在《兴安府志》卷八《艺文志》中收录的《创建三台书院记》,详细记载了其“延名师,置学田”的教育实践,与联语中的“训迪传衣钵”形成实践呼应。
白族家族文化中的“传衣钵”概念,既有佛教禅宗的渊源,又融合了儒家道统观念。明代李元阳《中溪家传汇稿》记载的“衣钵相传”事例,显示这种文化隐喻在科举家族中的普遍应用。赵甲南作为“岁贡生”,其身份处于科举体系的中端,联语既肯定其已获成就,又激励其继续进取,符合清代科举阶梯式晋升的特征。
通过地方志、族谱与官档的互证研究,赵廷俊联语的归属及其与赵甲南的关系得以清晰呈现。这一研究不仅还原了清代滇西士族的文化生态,更揭示了科举制度下家族文化传承的微观机制。赵廷俊联语作为科举文化的物质载体,其背后隐藏的家族记忆与历史逻辑,为我们理解清代边疆社会的文化整合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赵廷俊生平事迹钩沉与联语创作背景
(一)仕宦经历与文学实践的双重维度
据《云南通志》卷一百七十六记载,赵廷俊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科中举,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进士,初授陕西汉阴厅抚民通判,后迁兴安府同知。陕南地区在清代属文化边缘地带,地方官员多承担教化职能。据《汉阴县志》卷三《职官志》载,赵廷俊在任期间“捐俸修葺学宫,置义田以赡寒士”,其联语中“训迪”主题正与此相呼应。道光七年(1827),其主持重修汉阴文峰塔,碑文载“士子登科及第者,接踵而起”,可见其教育实践成效显著。
赵氏家族学术传统深厚,《赵氏族谱》载其六世祖赵珤(1469-1544)为明代著名理学家,与蔡清并称“赵以愚,蔡以虚”。《明儒学案》卷四十五记载赵珤“以格物致知为宗,尤重实践”,这种家学渊源深刻影响了赵廷俊的文学创作。其联语“诗书教子黄金贱,道德传家清誉香”(见《云南楹联名作选》),正是对理学思想的文学化表达。
(二)联语创作的政治隐喻与文化基因
赵廷俊现存联语42副(据《大理历代楹联集成》统计),其中科举主题占比达38%。“鹏程远报紫泥封”句中,“紫泥”典出《后汉书?光武帝纪》“奉紫泥之诏”,代指皇帝诏书。清代科举制度下,进士及第者常获皇帝直接任命,如《清史稿?选举志》载“殿试传胪后,新进士需至保和殿朝考”。赵廷俊本人由进士入仕的经历,使其对“紫泥封”的政治意象有深刻体认。
联语中“荆树”“燕山”等典故的运用,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交融。“荆树”出自《续齐谐记》田真兄弟分荆典故,象征家族团结;“燕山”则典出《宋史?窦仪传》窦禹钧五子登科故事,强调教育传承。这种用典方式与江南赵氏楹联“集帖为联”的创作传统高度契合,如赵之谦《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所收联语,即大量化用经史典故。
(三)交游网络与文学社群的互动关系
赵廷俊在陕南任职期间,与中原士大夫多有交往。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卷十八记载,其与陕西巡抚卢坤(1772-1835)过从甚密,曾参与编纂《秦疆治略》。卢坤在《秦疆治略序》中称赵廷俊“学通今古,才优干济”,可见其学术地位。此外,其与江南学者钱泳(1759-1844)亦有书信往来,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一载其联语“云影波光天上下,松涛竹韵水中央”,体现出江南园林美学对其创作的影响。
大理文人圈层的互动同样值得关注。据《滇南诗略》卷二十四记载,赵廷俊与李元阳后裔李于阳(1781-1846)结为诗社,其联语“文笔千寻摩碧落,墨池万顷壮沧溟”(现存大理文献楼),与李于阳《苍洱丛谈》中“点苍文笔,实为滇南文运之脉”的观点互为印证。这种文学互动形成了地域性创作范式,如《云南通志稿》卷一百七十一载“太和联语,多宗唐人格调,间融宋儒理趣”。
赵廷俊联语创作具有三重学术价值:其一,作为清代边地官员文学的典型样本,其作品反映了科举制度对地方文化的塑造作用;其二,南北文化交融的创作实践,为研究清代文学地理提供了鲜活案例;其三,理学思想的文学转化,展现了儒家文化在西南边疆的传播路径。其联语“种竹似培佳弟子,爱花如护小才人”(见《大理古联选注》),至今仍被大理中小学作为校训使用,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
赵廷俊的联语创作,既是个人仕宦经历与家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清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通过对地方志、族谱及档案文献的钩沉,我们不仅得以还原一位边地官员的文学世界,更能透视科举制度、家族传统与地域文化的复杂互动。这种研究范式,为传统楹联文化的现代阐释提供了新的学术路径。
三、联语意象解析与大理文化语境
(一)家族伦理的文学建构:以“荆树栽培”为中心的考察
《赵氏族谱?家训》载:“吾族自明季迁居大理,累世以耕读传家,尤以敦睦为本。”这与联语中“荆树栽培”的意象形成互文。“三荆同株”典故出自《续齐谐记》,喻指兄弟和睦。据《云南通志》卷二十四记载,明代大理赵氏家族赵珤“幼孤,赖叔父廷玉教养,弱冠登弘治丙辰科进士”,其成长经历正是“荆树栽培”的生动诠释。赵珤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其《居家杂仪》强调“族中子弟无论贫富,必令读书”,这种家族教育理念在清代得到延续。
清代《大理府学志》显示,赵氏家族在喜洲建有“荆树书屋”,作为族中子弟肄业之所。光绪年间举人赵甲南入学时,其伯父赵廷俊撰写此联,既表彰其学业成就,更暗含“兄弟同枝”的家族期待。族谱记载,赵甲南兄弟七人中有五人考取功名,印证了“荆树栽培”的实际成效。这种以树木意象隐喻家族伦理的书写传统,在白族文人作品中屡见不鲜,如邑人李元阳《感怀诗》“庭前双桂树,根柢自连蜷”,即通过植物意象表达宗族观念。
(二)科举教育的文化符号:“燕山训迪”的双重隐喻
“燕山训迪”典出《三字经》窦禹钧教子故事,联语中“传衣钵”三字暗示赵氏家族存在严格的教育传承体系。据《清代云南乡试录》记载,赵氏家族自顺治至光绪年间共有17人中举,其中赵廷俊本人为道光乙未科进士,历任广西学政。这种科举成就的取得,与家族教育机制密切相关。族谱《艺文志》收录赵廷俊《示儿书》云:“吾家虽为白族,然诗书传家不异中土,汝曹当以窦氏五子为范。”
大理地方文献记载,赵氏家族设有“延贤馆”,专门延聘江浙名师教授子弟。光绪《赵州志》载:“赵廷俊致仕归里,捐银二千两扩建族学,购经史子集千余卷。”这种教育投入在科举上的回报显著,赵甲南于光绪十九年中举,其试卷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批语有“根柢深厚,不愧家学渊源”之语。联语中“传衣钵”的意象,既指涉佛教禅宗的衣钵相传,更暗合科举时代的文化资本传承。
(三)地缘文化的符号隐喻:“绿野堂”与“凤凰毛”的双重指向
“绿野堂”典出唐代裴度别墅,联语中既指涉赵氏家族园林建筑,更暗含隐逸文化的价值取向。《大理县志稿》记载,赵氏宅院“绿野堂”建于乾隆年间,“前临洱海,后枕苍山,中有藏书楼三楹”。这种园林布局体现了“城市山林”的士人理想,与喜洲严家大院、董家院等建筑共同构成大理士族文化景观。值得注意的是,“绿野堂”中设有“桂香书屋”,与联语“燕山训迪”形成空间呼应。
“凤凰毛”意象融合了汉族典籍与白族神话。《庄子?秋水》“鹓雏非练实不食”的典故,在联语中转化为对族中才俊的期许。而在白族文化中,凤凰被视为“神鸟”,《白古通记》载:“凤凰鸣于点苍,兆大理文风昌隆。”赵廷俊作为白族士人,巧妙将二者结合。光绪《云南通志》记载,赵氏家族“每岁中秋,集族中子弟于绿野堂,以凤凰为题课诗”,这种文化实践强化了联语意象的象征意义。
(四)历史事件的潜在关联:家族政治的延续性考察
联语创作背景与清代大理科举兴衰密切相关。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统计,清代云南进士共698人,其中大理府占137人,赵氏家族独占11人。这种科举优势在联语中转化为“传衣钵”的文化自信。值得注意的是,赵廷俊之侄赵廷标在民国《大理县志》中记载为“民国初年省议员”,显示家族政治影响力的延续。这种“科宦蝉联”的现象,与联语中“燕山训迪”的教育理念形成因果关系。
明代赵珤家族“一门三进士”的荣耀,在清代转化为更系统的教育规划。族谱《族规》规定:“族中俊秀年及束发,须入族学肄业;乡试之年,族中资助盘缠。”这种制度性保障使赵氏家族在科举竞争中保持优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显示,赵甲南历任四川綦江知县,其施政记录中多有“兴文教、重农桑”的举措,正是家族教育理念的外化。
赵廷俊联语通过“荆树”“燕山”等典故的创造性运用,构建了一个包含家族伦理、科举教育、地缘文化的多重意义空间。这种文学实践不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是大理士族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地方志、族谱与档案文献的互证,揭示了联语背后复杂的历史脉络,为理解西南边疆地区的家族教育传统提供了典型案例。这种将经典意象本土化的创作策略,体现了白族士大夫"和而不同"的文化智慧,对于研究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联语的多重意蕴与赵廷俊的历史定位
赵廷俊所撰勉励赵甲南的联语,绝非简单私人文本,而是清代大理士族文化生态的生动映照。据《大理丛书?赵氏族谱》记载,赵氏家族在大理根基深厚,文化底蕴代代累积。联语中“三岛”,于光绪《云南通志稿》等大理地方志里,指洱海三岛,承载白族地域文化与精神信仰,是白族文化符号代表。“五华”关联昆明五华书院,传播中原文化,又契合白族文化元素,彰显边疆与中原文化交织。从《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可知,赵廷俊嘉庆二十一年中举后,任职多地推行儒家理念,《四川通志》道光版载其在彭水“建义学”、泸州“修县志”。归乡后,依大理府志,建赵氏宗祠并刻《论语》《孝经》。赵氏族谱家规明确子弟教育,使汉族典籍与白族本土文化相融。乾嘉时期大理府进士人数占全省43%(《明清云南进士碑录》),赵氏贡献突出。赵廷俊借此联,传递“耕读传家”“诗书继世”价值观,凝聚家族与地域文化认同,展现边疆士人在中华文化共同体中的积极作为。
参考文献:
[1]段金录.大理喜洲白族“诗书继世”的家风传承——以喜洲赵氏家族为例[J].大理大学学报,2021,7(9):42-47.
[2]马居里.明清时期云南大理地区的科举文化[J].学术探索,2019(10):129-134.
[3]杨政业.白族文化史[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
[4]顾廷龙.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M].中华书局,1992.
[5]傅璇琮.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来源:翠微吟社
编辑:赵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