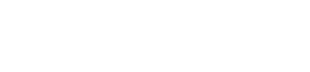徐 耿 华 先 生 简 介

徐耿华,1947年生,陕西省周至县人。现为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兼散曲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华诗词学会高研班十大导师之一,荣获中华诗词学会2020年“聂甘弩杯年度诗坛人物”。
情真·语谐·味浓
——张存寿散曲风格初探
徐耿华
我与张存寿同志相识相交已有十数载,个中缘由就是都爱散曲。我初识存寿时他还在部队某院校当领导,可在我看来他已经“移情别恋”了,爱上了与自己本职工作距离较远的散曲。他说:散曲上手是2012年,现在也有上千首。所写的内容无非是言志、抒怀和寄思。他在公务繁忙之余,尚有千首之作,足见其乐此不疲,着实令人佩服。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退休后,张存寿到中华诗词学会当领导,分管工作中就有散曲创作,更加地如鱼得水,大有可为了。
张存寿的散曲作品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对人生坎坷经历的感悟,有对祖国山河的礼赞,有对改革开放的讴歌,有对人民生活的关切,有对风物民俗的描摹,有对人间真情的诉说,也有对邪恶势力和不良现象的嘲讽和鞭挞。若论风格,我以为张存寿的散曲是情真、语谐、味浓。

发自肺腑,为情造文
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自己的美学观点:“情者文之经”,“为情造文要约而写真”。强调情感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紧密关系,主张写东西应该出乎真情,要写出自己的真性情。明代袁宏道也说:“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叙小修诗》)张存寿写曲显然是深谙此道,他的很多作品都能发自肺腑,为情造文,感人至深。
记得很多年前,我曾读过张存寿的两篇套曲《思母情》和《忆故乡,念爹娘》,至今印象颇深。他出生在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贫穷的小山村里。在那个“吃不饱”的岁月里家境困难,“怨父硬心肠,念母好慈祥。儿女学堂住,双亲碗里糠。赊粮,父与天争亮,拾荒,娘与蜂比忙。”(〔得胜令〕)然而,青年时代的张存寿心胸壮阔,志向高远,终于有机会高考入伍上了军校。离家前“盼儿飞昼思夜想,送女走叹短吁长。父不开腔,母理衣箱,一嘴叨叨,两眼汪汪”。“甘来苦去家门儿幸,微身高中龙门儿应,爹欢娘笑神牌儿供,从今坐上公家的凳。大姐凑盘缠,大嫂包糖粽,连哭带笑相跟着送。”(〔塞鸿秋〕)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场景啊!尽管语言直白,却能打动人心,皆因发自肺腑、情意浓烈之故。再看他远离家乡数月后的感受:“守家旷日烦鸡犬,出户当秋盼父兄,说甚个鹏程!”这大概是许多走出农村的青年们的共同感受吧,笔者我便是如此。
张存寿很擅长抓住一些小事描写亲情,如写《孙子在家》:“丢开锅盖玩壶盖,‘陀螺’转的溜溜快,啪嚓一响壶歇菜。呜哇一个怜人态。奶奶揽怀中,反把爷爷怪:早该摔坏你没摔坏。”(〔正宫·塞鸿秋〕)刘庆霖先生点评说:短短四十几个字写了三个人物,有叙述、有描写、有形态、有真情;无说教、无做作、无费话。较好地体现了生活是泥,诗是陶。
再如他的《女儿寄手机》:“女儿万里遣人急,不送吃喝送手机。左瞧右看真得意,偏说她费糜。不开封留个心思。爹娘老,儿女稀,就赚个贴己棉衣。”(〔双调·水仙子〕)人常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小棉袄送给他一款价值不菲的手机,明明是爱不释手,甚至“不开封留个心思”,却要说女儿太过“费糜”,不懂得勤俭度日。作品把“父亲”获得女儿送来手机后的喜悦心情描写的细致入微,令人拍案叫绝。
张存寿退休前一直在部队工作,因而写过很多反映当代军人的生活的作品,许多作品还很感人。如写《将校蹲连》:“叹一番将校蹲连。赤脚耕田,晓暖知寒。为士三周,列兵今日,元帅当年。夜相和呼噜竞喊,昼相伴血性擎天。一日三餐,同淡同咸;一去三还,无语垂涟。身返围城,梦里排班。”(〔双调·秋风第一枝〕)这是一首非得有亲身经历后才能写出的作品。将校蹲连,与班排战士同吃同住同操练,“夜相和呼噜竞喊,昼相伴血性擎天”。离开时“一去三还,无语垂涟”,离开后“梦里排班”。这是多么深厚的官兵情感!再次验证了“情至之语,自能感人”的至理名言。

趋俗尚趣,本色语言
张存寿的散曲语言趋俗尚趣,他说:“散曲讲究语言直白通俗,如果一般去拉家常咸淡,整篇读完还是白开水,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所以尽可能俗中出趣。句子出趣,整体有趣。”他的这种对散曲语言的追求,正是对元代散曲本色派先贤语言风格的赓续和继承。元人周德清谈到散曲语言时说:“造语必俊,用字必熟。太文则迂,不文则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要耸观又耸听。”(《作词十法·造语》)清人黄周星也说:“曲之体无他,不过八字尽之,曰:少引圣籍、多发天然而已。”(《制曲枝语》)张存寿散曲中没有拗口晦涩的句子,只有流畅明快的语言。如他的《再吃高密炉包》:“头回装个文人范,轻轻一咬连连赞。二回酒上桃花面,腮帮不问皮和馅。满桌无美人,再要一头蒜,减肥大事明儿干。”(〔正宫·塞鸿秋〕)由于饭桌上没有美女,不怕满口蒜味儿讨人嫌,于是乎“再要一头蒜”,至于减肥大事只好留给明天。
如果说用雅俗共赏的语言写散曲还较容易,做到俗中有趣就就很难了。所谓语言之趣,就是读后使人感到愉快,能引起兴趣,它涵盖了情趣、意味等多个方面。清黄周星《制曲枝语》中说:“制曲之诀,虽尽于‘雅俗共赏’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古云:‘诗有别趣’,曲为诗之流派,且被之弦歌,自当专以趣胜。”关于散曲的趣味性,赵义山教授总结为讽刺之趣、描写之趣、构思之趣、修辞之趣(比喻、夸张等)。如元人讽刺当时德不配位的高官,“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这是比喻;写大蝴蝶,“轻轻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这是夸张;写贪小利者,“鹌鹑膆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这是嘲讽。
张存寿写散曲熟悉此道,所追求的就是俗而有趣。如他的《〔正宫·塞鸿秋〕戏看冰壶比赛》:“当头一个汤婆子放,两边四个拖仪仗,汤婆子款款出营帐,有人跪做微臣样。汤婆子直向前,打前的急跟上,紧擦地板把娘娘让。”把体育器械冰壶比作大号的“汤婆子”(暖壶),而这个“汤婆子”似乎有王母娘娘那样高贵地位,它出帐时有仪仗跟随,有“微臣”跪,紧擦地板的还要把娘娘让。这是多么活灵活现的比喻,读之令人捧腹。
再如他写《甩锅家》:“三扔四甩怨张飞,张口结舌学李逵,无可奈何连锅烩。都知锅认谁,你砸他、何用咱赔。留下涂涂粉,腾空蹭蹭黑,给大兵凑个钢盔。”(〔双调·水仙子〕)此曲用嘲讽的口气,把美西方的甩锅家卑劣伎俩分析得淋漓尽致。明明是自己的问题,却总想把黑锅扣到别人的头上。他们学着李逵的口舌,把锅甩给相差八九百年的张飞,足见其胡说八道。反正老子天下第一,锅甩砸了也“何用咱赔”。遇见不好惹的,总能给你脸上“蹭蹭黑”;遇见好欺负的,这个锅说不定能给自家的大兵做个钢盔,直接打了过去。
阅读张存寿散曲,这种让人忍俊不止的作品俯拾皆是,如《草原山坡驴的纠结》《等灯》《我做闷面》《晚舟将归》《挑西瓜》等,足见其对散曲趣味的执著追求。

立意深远,豹尾味浓
古人总喜欢用味道浓淡来评价文学作品,立意深远、语言隽永者谓之味浓,反之为味淡。北宋刘攽《中山诗话》说:“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清人王夫子也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 披览张存寿散曲,不难发现他的很多作品都立意深远,余味无穷。这与他深邃的思维和广博的学识不无关系。捡其广为流传者罗列几首:
《〔双调·水仙子〕铅笔》:“皮光心硬赤条条,得用之时先对刀。出头总把头磨掉,钻尖不仰高。小擦儿偷抹功劳。才有圆滑相,便来冷眼瞧,躲不过又得挨削。”
明眼人一看便知,此曲绝非单纯地写铅笔,而是有很高的立意。铅笔,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书写工具,在曲中它成了社会最底层的、脚踏实地的劳动者形象的代表,而“小擦儿”(橡皮)却是他身边嫉贤妒能、颠倒是非的小人。可怜的铅笔“得用之时先对刀”,刚刚出头就得“把头磨掉”,而且常常被“小擦儿”污蔑、诽谤、“偷抹功劳”。尤其是铅笔的主人,时不时地对铅笔冷眼相加,“才有圆滑相,便来冷眼瞧,躲不过又要挨削”。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和事少吗?铅笔之哀,小擦儿之恶,职场之弊,不言自喻。
再看《〔中吕·山坡羊〕动物园猴王》:“双腮没肉,便宜没够,拥妻抱妾搔头秀。眼无羞,嘴无休,上蹿不怕臀红厚,下跳敢冲游客吼。吃,不用愁,喝,不用愁。”
此曲惟妙惟肖地出勾勒出一副贪腐者的无耻形象。猴王暗指有权有势的人,否则如何称王称霸。这些人贪欲无度,“便宜没够”。他们中不乏拥有三妻四妾者,大搞权色交易。他们不愁吃不愁喝,整日里上蹿下跳,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却还“嘴无休”,用最漂亮的话术说教别人。元人杨载说“咏物之诗,要托物以伸意。”(《诗法家数》)张存寿正是借写动物园猴王来揭露贪腐者的丑恶嘴脸。
张存寿写曲十分注重打造结尾。他说,自己的许多作品是先有了满意的结尾,才去把前文的铺垫补齐。古人把这种寓意悠远、令人深思的结尾称之为“豹尾”。元陶宗仪说:“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尾要响亮。”(《南村辍耕录》)张存寿就是一个竭力追求结尾响亮的人。
他写《〔中吕·山坡羊〕大暑日登娄山关》:“群峦环抱,尖山相照,一关尽为一词傲。路迢迢,热嘈嘈,因何不见西风闹?沿路蝉儿答的巧:天,烤过了;人,考过了。”
娄山关是兵家必争之地,红军长征时在此曾发生激烈战斗。然而真正让娄山关名满天下的是因为伟人毛泽东的词《忆秦娥·娄山关》,“一关尽为一词傲”。作者张存寿登关凭吊时正逢大暑,酷热无比,于是他想起伟人词作的首句——“西风烈”,问:“因何不见西风闹?”最称奇处是“沿路蝉儿”回答这个问题:“天,烤过了;人,考过了。” 天烤过了自然是指当时的暑热天气,人考过了就寓意深刻悠远了。是指作者自己经受住了人生的考验,还是泛指共产党人执政后考了个好成绩,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因为当年伟人离开西柏坡时曾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
再如《〔双调·水仙子〕大院墙角老槐树开花了》:“偏居少遇剪一裁,根浅难承身半歪,有谁能把园丁怪。春天人不睬,夏临时香远袭来。花垂下,叶敞开,一树清白。”
从文字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一首描写老槐树开花的小曲,而实际上这是一首作者的自谕之作。张存寿少年时“偏居”一个小山村里,由于没有根基只能守身持正,因为他担心“根浅难承身半歪”。对此,他没有“把园丁(喻指父母或领导)怪”,通过自己努力,从一个“人不睬”的无名之辈迎来了人生的高光年代,正所谓“花垂下,叶敞开”。特别要紧的是结尾“一树清白”,表面上是说槐花开了一树清白,而实际上是对自己一生为人做事的自许和宽怀。
总之,张存寿散曲不同凡响,读之令人口舌生香,望作者写出更多脍炙人口的好作品来。
张 存 寿 先 生 简 介

张存寿 1962年生,山西昔阳人。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党支部书记,原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军休干部,大校军衔。研究生学历。中华诗词学会十大导师之一。全军优秀党务工作者,获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纪念章。在各类报刊发表文学作品300多篇(首)。合著有《六味集》《中华诗词十二家》等书12部。
转自《瞿塘潮诗评》公众号